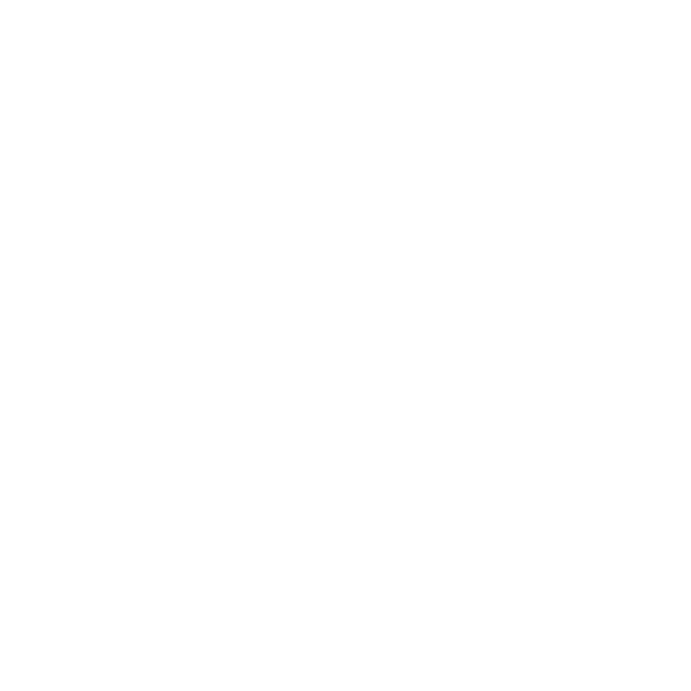【精神革命】走出文明衝突怪圈 須群策群力建設文化智商工程
/ 2019.04.11
【文章原刊於01撐場,歡迎下載香港01 app,與更多作者一同討論喜愛話題。】
近年來,世界各地有關文化衝突的消息不絕於耳。自從1990年代民族主義在全球範圍內重新冒起,針對全球化和族群融合的不滿似乎越演越烈,其利用互聯網等科技平台,在組織上、宣傳上形成新的攻勢,並開始佔據多國政壇主流。在英國,疑歐派成功劫持政治,堵死脫歐之外一切選擇。在歐洲大陸,反移民政治力量在德國建立極右 「另類選擇黨」,又促成奧班.維克多(Orban Viktor)領導的匈牙利右翼執政。特朗普上台後,處處針對中東和拉丁裔人,並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大有上升至新冷戰的勢頭。在中東地區,屬於遜尼派的伊斯蘭國針對什葉派和基督徒大開殺戒,終於多國干涉下敗亡。在中國,少數民族關係僵持不下,恐襲陰霾依然籠罩各地,而香港自身也面臨族群共融的壓力。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種種預言似乎在一一應驗。
特朗普上台後,處處針對中東和拉丁裔人,並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大有上升至新冷戰的勢頭。(Gettyimages/視覺中國)
可幸的是,局勢並不是一邊倒。在英國,教育水平較高的年青人普遍反對脫歐,德國社會上下也有不少歡迎、並積極採取措施容納中東移民的人士,而面臨民主黨左翼嚴峻挑戰的特朗普,能否捱過第二次選舉,尚屬未知之數。這些能夠接納異文化的社會力量,特別之處到底在哪裏?社會為了走出文明衝突怪圈,應當促進哪些基本要素的增長?答案可能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洪洵(Soon Ang) 、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范戴茵(Linn Van Dyne)和組織管理心理學家 P. Christopher Earley三名教授所提出的「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Quotient, ‘CQ’)概念。
社會為了走出文明衝突怪圈,應當促進哪些基本要素的增長?(Gettyimages/視覺中國)
「文化智商」理論基礎
正如智商的定義是「掌握並準確判斷抽象概念並解決問題」(Schmidt & Hunter, 2000),洪洵和范戴茵(2009)把「文化智商」定義為「個人應付多元文化處境並在其中有效運作的能力」,並認為它是「全球思維」(thinking globally)和「在地行動」(acting locally)之間的橋樑。文化智商理論本來主要應用於跨國公司內部建構和國際商務來往,後擴展至教育界及政府行政領域上;理論者並且認為文化智商的建立可以製造「世界公民」,可以促進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和諧共處,也能提高政府效益,減少行政成本,並增進弱勢群體權益和社會總體安全穩定。洪、戴兩人利用Sternberg & Detterman(1986)的「智商多重心」(multiple foci of intelligence)框架,把文化智商(CQ)的構成形容為「四個中心」,即:
一、 CQ驅動力(CQ Drive),這決定個人有沒有興趣和信心去學習、適應、享受異文化經驗;二、 CQ知識(CQ Knowledge),即個人對文化、制度、價值、語言的異同有多少認識;三、 CQ戰略(CQ Strategy),屬於一種元認知 (Metacognition),即一個人如何切合文化異同,計劃並做出適當的行為,且根據現實情況適時調整;四、 CQ行動(CQ Action),即個人針對不同文化處境,建立一系列語言和行為反應,並正確應用之。
不同於部分取決於先天因素的智商(IQ)和情緒智商(EQ),文化智商完全可以後天建構。但文化智商的建立決不是個人的問題。明顯可見,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文化智商」,於日益嚴峻的族群關係和國家安全局勢下,已經成為不可再緩之圖,其必須被視為一項跨國的社會系統工程,在有效國際合作、有力政治指導和社會各界積極推動下,盡快在各國全社會中建立起來。
不同於部分取決於先天因素的智商(IQ)和情緒智商(EQ),文化智商完全可以後天建構。(Gettyimages/視覺中國)
建立文化智商是社會系統工程
Shannon & Begley(2009)認為,學習語言、外地工作經驗、社交圈子多樣性都有助於提高文化智商。然而,這些機會顯然不是人人皆有,很大程度取決於個人的社會經濟背景,以及當地政府有沒有採取積極文化措施。英國的例子正好說明,政府必須在這些方面積極進行干預,填補社會經濟差異,而干預的成果也往往立竿見影。英國的種族關係曾經惡劣不堪。在七、八十年代,種族暴動幾乎每年一度,政壇也為疑歐保守力量所把持。然而事到如今,曾就讀大學的英國年青人普遍反對脫歐,思想傾向多元、多種族主義,這是當局多年來努力積累而成。1965年英國通過《種族關係法》,將歧視非法化,為推動各種共融措施和第二代移民的中產化製造條件。英國教育當局改革了GCSE(中學會考)宗教科課程,從以前的「聖經」課綱,改為教授各主要宗教、包括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從小培育學生的CQ知識和驅動力。英國在1987年也開始參與歐洲共同體(後歐盟)的伊拉斯謨計劃(Erasmus Programme),大額資助英國和歐洲各地大學生和體育專才進行交換,拓寬視野,並培育歐洲認同感。
英國教育當局改革了GCSE(中學會考)宗教科課程,從以前的「聖經」課綱,改為教授各主要宗教、包括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從小培育學生的CQ知識和驅動力。(Gettyimages/視覺中國)
社會經濟條件決定文化智商能否有效建立;反之,文化智商雖然不能直接解決經濟基礎問題,但考慮到文化、制度往往反作用於經濟基礎,文化智商最後也跟經濟關係密切。脫歐和種族矛盾造成的經濟動盪就是慘痛例子。以前為人稱道的幾種文化融合政策,比如社會主義國際主義(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美國「文化熔爐論」、法國「共和主義同化論」、都在蘇東、南斯拉夫瓦解、特朗普上台、法國恐襲浪潮底下相繼破產。原因在於過往的融合政策只談社會整體和族群文化版塊,而鮮有貫徹到個人層面,甚至要自欺欺人,假裝個人與個人之間可以變得毫無文化差異。法國的同化政策,因此只能反映巴黎精英的傲慢。文化智商的建立,作為一種「自下而上」、講求個人素養、充分承認人際文化差異的辦法,可謂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社會建設的定海神針。這裏需要的是政治的決心和策略。跨國機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推動、協調全球範圍文化智商提升的系統工程中,可以扮演重要作用。在往後一系列文章中,筆者將會提到幾個在文化智商上曾經領先世界、卻經不過考驗而崩潰的多民族多信仰國家──鄂圖曼帝國、奧匈帝國、南斯拉夫;以及成功的案例,如新加坡,到底是怎麼一路走來的。
新加坡到底是怎麼一路走來的?(Gettyimages/視覺中國)
文化智商及其敵人(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its Enemies)
正如「開放社會」(Open Society)有其敵人,文化智商的建立,也不可能無往不利,其四個重心──CQ驅動力、CQ知識、CQ戰略和CQ行為──反面分別是「文化索然」(Disinterest)、「文化無知」(Ignorance)、「文化無謀」(Tactlessness)和「文化無為」(Inaction)。建立文化智商,作為為政者的一項政策,和一場由各階層各族群共同參與的全社會運動,必須向這四個反面進攻,從個人層面瓦解一切因無知、恐懼、不作為而造成的文化反動(cultural reaction)及其政治、經濟表現,包括消極保護主義和偏安思想。這呼喚着一種開明而強勢的政治,敢於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跟那些推動文化無知、恐懼、民粹和不作為的政客和群體周旋鬥爭,決不能含糊其詞,允許運動變得模陵兩可(wishy-washy)。同時要清楚區別,這些文化群體對當局到底採取謹慎開放、還是純粹保守的取態,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要盡量爭取多數,孤立頑固的一小撮。
接納異文化必須有原則,不能使之成為個別群體內部保守力量的護身符。以最近意大利新法西斯主義者反吉普賽人的暴動為例,當局在推動社會接納文化差異、打擊新法西斯主義的同時,應確保吉普賽人住房、就學、就業平等權益,動用行政資源強制吉普賽家庭住進公營房屋、強迫家長送兒童上學,破除吉普賽人對上樓和就學的禁忌。只有如此,文化差異才不會在長遠演化成制度性和政治經濟差異,變成跨代貧窮的原因。也只有如此,文化差異才可以在無尊卑的平等基礎上存在。如此強勢政治,必須充分民意基礎。推動文化智商增長的運動,首先應由社會跨文化組織倡議推動,然後由主要政黨牽頭,在其執政之日動用行政資源,在全社會範圍有計劃、有協調地進行。這也涉及到保障各文化群體中進步份子的參政議政的權利。但只有在建基於廣泛聯盟的情況下,推動文化智商建設的工程才不會適得其反,引起社會反感,也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推動這場精神革命,以消彌國家和社會安全隱患,並使社會得以穩步邁向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
接納異文化必須有原則,不能使之成為個別群體內部保守力量的護身符。(Gettyimages/視覺中國)
作者簡介:
梁明德@GLOs
1992年生,香港大學歷史、法文雙主修畢業。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生哲學碩士,其研究對象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中日關係。
GLOs 集團旨在將國際關係產業化,業務涵蓋六大範疇:教育、研究、旅遊、生活、社會及創意;透過不同公司和品牌,成為國際間的橋樑,或有助社會大眾適應各地文化,促成企業間合作關係。集團以協助小眾群體建立關係為重,跟跨國界人士合作,如非洲、南美洲,發掘其獨有才能。教育範疇將以共同學習人工智能(AI)、編程等方面知識納入課程,以適應未來科技世界。
【編按:文章題目為編輯所擬,原題為「推動社會 “文化智商” 增長 走出文明衝突怪圈」】
(以上文章內容均屬用戶提供,香港01不為任何用戶內容而衍生或遭受之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