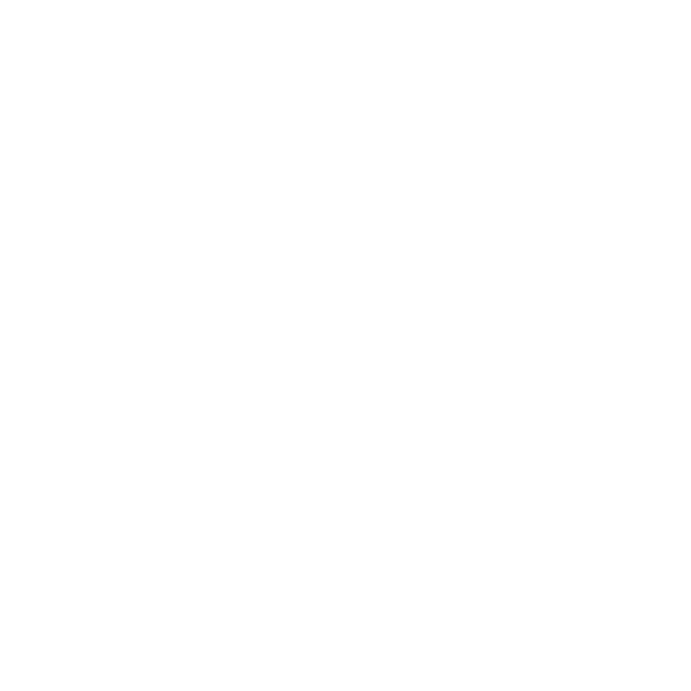回溯「廣東抽象」:問題緣起與藝術家評點
/ 2018.04.20
本欄目的第一篇為大家帶來「廣東抽象」這個概念。2017年末到2018年3月之間,由嶺南美術館、關山月美術館、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共同主辦,楊小彥、葉向明、胡斌聯合策展的「回歸本體:廣東新時期抽象型藝術溯源」展出了近40位藝術家的作品,旨在系統地回顧發生在廣東地區改革開放以來抽象藝術發展的全過程。
楊小彥-批評家,策展人,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州美術學院客座教授
我們揀選了策展人之一楊小彥教授的文章,為讀者解答以下問題:
(一)抽象繪畫看起來只是隨意塗抹、廢除了具體事物形象,究竟有什麼好欣賞的?它在中國當代藝術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為什麼在中國,抽象繪畫至今依然會成為一個「問題」?
(二)「廣東抽象」這個概念指的是什麼?包括了怎樣的藝術個案?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脈絡中,廣東抽象有什麼特別的審美價值?
就藝術而言,抽象是一個問題。
當年我在廣州美院就讀藝術理論研究生,遲軻老師佈置的課業之一是翻譯西方藝術理論,我其時翻譯了康定斯基《回憶錄》中的一段,希望通過他的親身經歷瞭解與認識抽象藝術,包括意義與價值。在回憶中,康定斯基生動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畫出人類藝術史上第一幅抽象畫,是什麼原因刺激他走出這決定性的一步,以及應該如何解釋與理解抽象藝術。
在這裡,我想先把當年翻譯的其中一段引用如下,正是在這一段文字裡,康定斯基交待了他創作時的內心動機:
「先前我只知道寫實主義藝術,事實上這就是那些清高的俄羅斯人的藝術,這種藝術在相當長的時期裡總是面對著列賓為佛朗茲·李斯特所畫的肖像中的一隻手和諸如此類的東西。可突然我第一次看到了莫内的畫。展覽會目錄告訴我,畫中對象是乾草堆,可我沒能認出來,這對我真是痛苦,我以為畫家沒有權力畫得如此含混不清,我模糊地感覺到,畫中物件正在消失。在一片驚惶和混亂中,我注意到這幅畫不僅吸引了我,還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它完全出人意料地呈現在我的眼前,甚至連最末一個細部也難以放過。所有這些如同迷霧一般,使我不能從中得出什麼簡單的結論。我唯一清楚的是,調色板具有不容置疑的力量,這種力量到那時為止對我還是莫測高深的,並超過了我的所有想像。繪畫需要神奇的力量和榮耀,客觀物作為繪畫必不可少的因素,不知不覺受到了我的懷疑。」
康定斯基,《構成第八號》,油彩,畫布,140 X 201 cm,1923 年美國紐約古根漢美術館收藏
康定斯基的《回憶錄》樸素而真實。令我詫異的是,他寫的這一段,居然和我的感受幾乎一樣!我甚至覺得他就是在說我。當然,我沒有康定斯基的才氣,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所處的藝術環境也和世紀初的康定斯基完全不一樣,他果敢地拋棄了傳統藝術對物象的依賴,棄絕客觀物在繪畫中的價值,我則花了很長時間去研習西方抽象藝術發展的歷史,理解這個俄羅斯藝術家的思想,以及他之後一大批持續推進抽象藝術發展的藝術家的獨特實踐,他們有的是抽象藝術家,有的則游離在抽象與具象之間,有的則超越了純粹的抽象。這個名單很長,其中有蒙德里安、杜斯保、納吉、克利、米羅、馬列維奇、波洛克、羅斯科、德.庫甯、史密斯、賈德、鐘斯、塔皮埃斯,等等,等等,以及更多的中國追隨者們。
回想起來,1978年我進廣州美院油畫系時,只知道寫實主義,崇尚俄羅斯巡迴畫派,瞭解列賓的主題畫創作,熟悉列維坦描繪俄羅斯自然的抒情風格,嚮往蘇裡科夫對歷史的複雜態度。我至今都不能忘記,當我第一次在同學那裡看到臺灣「新潮畫庫」系列叢書中《康定斯基》專輯時所產生的強烈震動,因為當時我完全不能理解,在寫實主義之外居然還有抽象藝術的存在。我沒有藝術家的敏感,可以立時感受到新的可能,我只是懷疑,像這樣的塗抹,怎麼可能比《伏爾加河的縴夫》、《伊凡.雷帝殺子》、《庫爾斯克省的祈禱行列》、《近衛軍臨刑的早晨》、《在寂靜的墓地上空》、《通向佛拉基米爾之路》等作品更加精彩?!放下這些俄羅斯的寫實名作不說,康定斯基的抽象藝術至少也不能和倫勃朗的《夜巡》、委拉士貴支的《紡織女工》、籍裡柯的《梅杜薩之筏》相比!當然,今天我已經充分認識到,寫實主義就像是一個想像的框,人被框住之後,很難從中逃脫出來。這是因為,一旦我們把藝術理解為表達客觀物象的一種媒介時,其實已陷身在物件之中,我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如何更精確地去表達所面對的主題,它們的存在、質感、造型、空間與色彩之間的關係,等等。我們很難想像,還有一種沒有客觀物像的抽象藝術存在。
後來我之所以轉到藝術史與藝術理論的學習,恐怕和初次接觸康定斯基藝術時所產生的震動與困惑有關。我想從中解套,瞭解抽象藝術的歷史,進而掌握現代主義藝術的發展脈絡,體認其中的價值變遷與社會進步的關係。藝術史的好處是,研究者試圖通過對不同時代不同的作品的認識,展現一個風格演進的邏輯序列,而不是只憑主觀猜測與想像。藝術史告訴我們,自從康定斯基在二十世紀初畫出第一張抽象畫以來,以及他寫作《藝術的精神性》以來,關於抽象主義的理論建構已經卓有成效,不僅本身分裂出所謂「冷抽象」與「熱抽象」的不同方向,而且也形成了基於不同地域、時期與具體目標的不同流派,相關研究也汗牛充棟,至少在二戰之後,抽象藝術已經不再是純粹的先鋒,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也就是說,就西方藝術而言,抽象不再是一個問題。
那麼,為什麼抽象仍然是藝術中的一個問題?我之所以這樣說,其實是有針對性的,那就是,在中國的藝術語境中,抽象藝術仍然是一個問題。
在研究二十世紀中國藝術的過程中,我強烈地意識到,影響中國近百年藝術發展的首先是「寫實主義」而不是其它。或者可以這樣說,正是「寫實主義」藝術運動,形塑了中國今天整體藝術的基本面貌。當然,我在這裡要申明,我所使用的「寫實主義」,甚至包括「寫實」這個概念,完全是中國藝術語境中「西方」概念,和西方藝術的實際發展沒有太大的關係。也就是說,我們是通過這一概念去理解西方藝術的,而且很多時候還是整個的西方藝術,儘管在藝術史的意義上,這一理解基本上是誤讀的結果。從這一層意義看,我們也可以說,所謂「寫意」,作為「寫實」的一個對立性概念,也是誤讀的結果,是在誤讀西方藝術的背景下對中國藝術的再次誤讀。也就是說,當我們輕率地使用「寫實主義」和「寫實」這樣一些概念時,當我們強調抽象和表現,以及背後的「純粹藝術」的審美性質時,我們說的其實是自己的事,是針對我們的藝術語境所做的一種概括,背後起作用不是藝術,而是持續變化的政治運動。同時,我還要指出,當我這樣說的時候,和是否理解、欣賞、提倡「寫實主義」藝術無關,更和所謂的藝術原創性無關。從文化史角度看,發生在我們的藝術現場的「寫實主義」藝術,包括其後的「現實主義」,以及改革開放時期的「新潮美術」運動,和這裡所討論的「抽象主義」,都必須納入到傳統社會崩潰、「民族/國家」重建的歷史演變當中,都是這一重大歷史與現實事件的必然產物。也就是說,百年中國的核心主題是革命,是觸及全體中國人靈魂的社會轉型,其涉及面之廣,以至於把所有領域都席捲其中,藝術自不能例外。在這裡,社會革命對於藝術之訴求,正在於動員與宣傳,藝術必須、也不得不成為革命有效的視覺工具。而作為工具,從接受的角度來看,只能是「寫實主義」及其相關樣式,而不可能是其它,比如「抽象主義」、「表現主義」或者「印象主義」之類。所以,正是社會革命本身而不是其它原因,確立了廣義的「寫實主義」在藝術中的正宗地位,這是不言而喻的。
作為「寫實主義」的反面理所當然是「抽象主義」,更準確地說,是各種抽象型的表現類藝術,其基本點是否定客觀物象在藝術中的核心地位,強調藝術自身的力量,強調藝術的自律性,強調藝術家與藝術風格的內在精神聯繫,一句話,強調藝術的情感功能,而拒絕藝術的工具性。
可以想像,在社會革命風起雲湧的關鍵時刻,在動員與組織群眾重建「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寫實主義」作為一種有效的視覺動員工具,的確是舉足輕重的。在那樣一個急劇變動的時代,「寫實主義」取得一邊倒的絕對優勢,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並且符合歷史身身的邏輯。有意思的是,歷史總是曲折而複雜的,在「寫實主義」取得絕對地位的同時,一方面,「抽象主義」在公開場合成為對立面而受到全面壓制,另一方面,因為抽象藝術自由的特性,所以,又成為眾多敏感的藝術家在表達個體情感方面的一種私人努力,用以對抗整體藝術的單一性。這一點構成了中國抽象藝術與西方不同的發展基點,也使得中國抽象藝術帶有某種「先天」的悲劇性。基於同樣原因,只有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抽象藝術才獲得基本的發展空間,藝術的多樣化也才能通過對不同的抽象風格的持續探討而重新得到肯定。
基於此我才認為,抽象藝術是一個問題,是一個中國藝術語境中、有別於西方藝術與理論的現實問題。也只有在這一背景中,中國「抽象主義」藝術運動才具有明確的「中國性」,因為其所針對的,恰恰是曾經的與當下的藝術現場,正是在這一現場中,中國抽象藝術才具有西方所不曾有過的「先鋒性」,成為獨立藝術的徵象,成為個性張揚的旗幟。
那麼,為什麼抽象仍然是藝術中的一個問題?我之所以這樣說,其實是有針對性的,那就是,在中國的藝術語境中,抽象藝術仍然是一個問題。
在研究二十世紀中國藝術的過程中,我強烈地意識到,影響中國近百年藝術發展的首先是「寫實主義」而不是其它。或者可以這樣說,正是「寫實主義」藝術運動,形塑了中國今天整體藝術的基本面貌。當然,我在這裡要申明,我所使用的「寫實主義」,甚至包括「寫實」這個概念,完全是中國藝術語境中「西方」概念,和西方藝術的實際發展沒有太大的關係。也就是說,我們是通過這一概念去理解西方藝術的,而且很多時候還是整個的西方藝術,儘管在藝術史的意義上,這一理解基本上是誤讀的結果。從這一層意義看,我們也可以說,所謂「寫意」,作為「寫實」的一個對立性概念,也是誤讀的結果,是在誤讀西方藝術的背景下對中國藝術的再次誤讀。也就是說,當我們輕率地使用「寫實主義」和「寫實」這樣一些概念時,當我們強調抽象和表現,以及背後的「純粹藝術」的審美性質時,我們說的其實是自己的事,是針對我們的藝術語境所做的一種概括,背後起作用不是藝術,而是持續變化的政治運動。同時,我還要指出,當我這樣說的時候,和是否理解、欣賞、提倡「寫實主義」藝術無關,更和所謂的藝術原創性無關。從文化史角度看,發生在我們的藝術現場的「寫實主義」藝術,包括其後的「現實主義」,以及改革開放時期的「新潮美術」運動,和這裡所討論的「抽象主義」,都必須納入到傳統社會崩潰、「民族/國家」重建的歷史演變當中,都是這一重大歷史與現實事件的必然產物。也就是說,百年中國的核心主題是革命,是觸及全體中國人靈魂的社會轉型,其涉及面之廣,以至於把所有領域都席捲其中,藝術自不能例外。在這裡,社會革命對於藝術之訴求,正在於動員與宣傳,藝術必須、也不得不成為革命有效的視覺工具。而作為工具,從接受的角度來看,只能是「寫實主義」及其相關樣式,而不可能是其它,比如「抽象主義」、「表現主義」或者「印象主義」之類。所以,正是社會革命本身而不是其它原因,確立了廣義的「寫實主義」在藝術中的正宗地位,這是不言而喻的。
作為「寫實主義」的反面理所當然是「抽象主義」,更準確地說,是各種抽象型的表現類藝術,其基本點是否定客觀物象在藝術中的核心地位,強調藝術自身的力量,強調藝術的自律性,強調藝術家與藝術風格的內在精神聯繫,一句話,強調藝術的情感功能,而拒絕藝術的工具性。
可以想像,在社會革命風起雲湧的關鍵時刻,在動員與組織群眾重建「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寫實主義」作為一種有效的視覺動員工具,的確是舉足輕重的。在那樣一個急劇變動的時代,「寫實主義」取得一邊倒的絕對優勢,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並且符合歷史身身的邏輯。有意思的是,歷史總是曲折而複雜的,在「寫實主義」取得絕對地位的同時,一方面,「抽象主義」在公開場合成為對立面而受到全面壓制,另一方面,因為抽象藝術自由的特性,所以,又成為眾多敏感的藝術家在表達個體情感方面的一種私人努力,用以對抗整體藝術的單一性。這一點構成了中國抽象藝術與西方不同的發展基點,也使得中國抽象藝術帶有某種「先天」的悲劇性。基於同樣原因,只有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抽象藝術才獲得基本的發展空間,藝術的多樣化也才能通過對不同的抽象風格的持續探討而重新得到肯定。
基於此我才認為,抽象藝術是一個問題,是一個中國藝術語境中、有別於西方藝術與理論的現實問題。也只有在這一背景中,中國「抽象主義」藝術運動才具有明確的「中國性」,因為其所針對的,恰恰是曾經的與當下的藝術現場,正是在這一現場中,中國抽象藝術才具有西方所不曾有過的「先鋒性」,成為獨立藝術的徵象,成為個性張揚的旗幟。
《回歸本體:廣東三十年抽象型藝術回溯》展覽海報
這一次策劃《回歸本體:廣東三十年抽象型藝術回溯》,志在系統地回顧發生在廣東地區改革開放以來抽象藝術發展的全過程,通過一系列的個案,突顯抽象這一問題在藝術中的意義,歷史性地張揚其中的審美價值。
翻檢歷史,我們知道,在老一輩藝術家當中,尤其是出生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的那一輩藝術家當中,極少有人從事抽象藝術實踐,即使更早一些的藝術家,二、三十年代出生的那一輩人,也少有人投身抽象藝術。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他們當中沒有人意識到藝術的本體性質,仍然有一些敏感的藝術家試圖尋找藝術自身的力量,儘管他們的作品很多時候並不太抽象,但存在於其中的物象,已經不再成為唯一的主題,而更多地變成了形式的載體。關於這一點,我想我們可以從三十年代的趙獸、關良、譚華牧、林風眠等人的作品中一窺其貌,無疑,他們是其後中國抽象藝術發展的先聲。而在廣東,出生在三十年代末的洪耀先生極有可能是他們那一代中難得的比較早就從事抽象型藝術探索的先行者,儘管遲至七十年代他才開始從事這一類風格的創作。
也就是說,開始從事抽象型藝術探索的或許是基於一種不無簡單的動機,那就是希望擺脫由來已久的寫實藝術的單一性,尋找新風格的可能。而在「寫實主義」氛圍中成長的藝術家,當他們轉向「抽象主義」時,寫實藝術一般會成為其明確的反叛對象,並以此為基點去構建屬於個體的精神世界。很多後來成長在多元藝術環境中的藝術家,則更自覺地把抽象藝術探索變為一種文化自覺,試圖摒棄過於一目了然的點線面組合,尋找更為本體的抽象語言的建構。
早在1977年洪耀就嘗試把魯班墨斗彈線轉化為藝術語言創作抽象繪畫。圖片為2014年藝術家在台灣新竹縣文化局美術館舉辦「洪耀彈線藝術」當代水墨展上作畫。
近幾年抽象藝術相當活躍,但活動多在北京和上海等地,這兩個地方也有屬於自身的代表性藝術家,廣東似乎相對冷清。但是,我在廣東成長,瞭解這裡的藝術情形,知道這根本就是一個假像,廣東,尤其在廣州,相比北京和上海,抽象藝術不僅沒有任何滯後性,而且,改革開放之後最早的抽象藝術實踐,很有可能是從廣州開始的。甚至,這一類實踐還可以追溯到更早階段。建國後就消失了的著名藝術家趙獸,因客觀原因隱居鄉間,以農民身份一直在進行抽象型藝術創作。我懷疑在運動頻繁的年代,尤其在極端時期,整個中國藝術界,可能只有他一個人在從事類似風格的探索。二千年後趙獸個展終於在廣東美術館開幕,展覽上有若干件抽象型作品,從標注日期看創作於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初期。當我駐足在這幾件作品面前時,我所感受到的力量已然超過了藝術本身,因為它們的存在,有力地見證了一種性格,一種不屈,以及一種對理想的長久堅持。同樣,作為五十年代廣州美院美術附中第一屆學生的洪耀先生,七十年代中期私底下開始從事抽象藝術探索,並很快就發展出了以線段為基本因素、通過線條彈跳而把墨色打在畫面上形成一種「自動」效果的獨特風格。他的這一類實踐,也是到了二千年之後才逐漸為人所知。曾經以寫實著稱的女畫家歐洋,九十年代初參加了法國華裔藝術家趙無極在浙江美院舉辦的油畫班之後,個人風格大變,意識到東方審美的重要性,從此以「意象油畫」為其探索方向,決心走一條屬於中國的油畫之路,儘管其間受到非議甚多,卻不改初衷,堅持至今,見證了一個老藝術家對於藝術的虔誠信念。從尊重歷史事實出發,我們必須承認,在「意象油畫」方面,歐洋是這一風格的重要先驅。甚至包括楊堯這樣的油畫前輩,八十年代中開始嘗試在廣州美院油畫系教學中進行抽象藝術教育,也因此留下了若干張畫於那個年代的抽象作品。稍後的藝術家何建成、鄧箭今、雷淑娟、陳海、石磊、方少華等人,儘管抽象不是他們的一貫風格,但也都在這一方向上一試身手,留下了若干重要的抽象型作品。所有這些跡象表明,廣東在抽象藝術領域的探索不僅不晚於內地,很有可能是領風氣之先。
洪耀,《弹水袖》, 宣纸,墨, 200 X 200cm, 2013年
梁銓,《清溪漁隱圖之三》,色、墨宣紙拼貼,140 X 200cm,2014-2015
值得特別一提的還有居於深圳的梁銓和嚴善錞,他們很早就在這一方向上努力。從作品看,我覺得已經不能用簡單的、偏於形式美感的抽象性來描述梁銓的藝術實踐,他對抽象的理解源自其對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精神性的獨特體認,所以,他很早就開始用一種組合的方式去創作,把紙性、墨性、水性等因素從原有形式中抽離,上升為一套互有關聯的藝術語言,從而讓作品具有抽象的構成感。從這一角度看,他的作品正是一種理念的集合,而與手繪之類的感性表現拉開了距離。嚴善錞一直在從事中國傳統文人畫的研究,在這這一方面成就斐然,一向為業界所稱道。不過,外人很少知道,他原來是一個孜孜不倦的藝術家,研究之餘,唯一興趣竟然是創作。嚴善錞學版畫出生,早年就讀於浙江美院版畫系,對版畫深有體會,此外,他是地道的杭州人,從小對西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兩相結合,於是就形成了他的繪畫風格,一方面把印痕作為語言,從不斷的印製中尋覓偶然性,並適時轉變為獨特的圖式,另一方面,他把這一圖式和西湖迷朦的氣氛相匹配,用以回應小從紮根內心的視覺記憶。從這一點看,嚴善錞的作品具有某種偶發的性質,他把抽象性貫徹到創作的全過程,去除表面的形式感。
對於廣東年輕一代的藝術家來說,抽象藝術更多是他們的一種審美自覺。
在女性藝術家當中,周力和周欽珊是兩個頗為意義的個案。從趣味看,她們似乎處於兩極,彼此對立。周力的抽象以線段為要素,通過複雜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在平面上的塗抹、在空間中的構成、在裝置裡的糾纏,形成了一種具有內在統一性的個人表達。關鍵是,她的塗抹、構成與糾纏本身就是多層次的,她就這樣,放任地讓情緒在這些個不同的層次中自由奔走,以形成不同的感受。周欽珊是一個邏輯性很強的藝術家,她的工作是一種冷然的介入,很長一段時間她是對自我的介入,探討作為女性藝術家與作為世俗女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然後,她在介入自身的基礎上,試圖以個人為出發點去介入社會,對那些足以引發公眾關注的事件加以「評論」。她不動聲色,不帶感情,不間斷地用鉛筆重複工作。在她筆下,短線組合成具有某種邏輯性的不同形狀的矩陣,不同的矩陣又互相配合以合成更大的矩陣。我一直懷疑她在這些個冷冰的矩陣組合當中,突然會沒有緣由地、間歇性地發出陣陣轟鳴,無聲,但有明顯的躁動在其中。
在這裡,還有兩個女性藝術家頗值得關注。何癸銳對形式和色調極其敏銳,她似乎有一種天生的能力,能夠把敏銳本身落實為對筆觸與材料的奇特控制,從而讓作品產生一種似乎可以通過觸摸而獲得的視覺質感。曾經留學法國多年的林芮襄在異國氛圍中滋長了一種對於東方情思的內心體認,她的想像來自對樸素調性的不斷描繪,讓複雜與單純交錯其中,從而獲得得審美的統一。
劉可,《2015第7號》,布面油畫、丙烯、織物染料、水性染料, 200 X 300cm,2015
柯濟鵬是個一以貫之的藝術家,他的創作就是日復一日、月複一月、年復一年的一絲不苟的描繪細線的過程,一張又一張,而且越畫尺寸愈大,一直大到他那小小的工作室無法容納為止。在抽象型藝術方面,劉可明顯地分成了前後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中,他的畫面依然有物象存在,他試圖通過一種細碎切割的方式去肢解這個物件,從而讓物件在觀看中隱退。也許這種方式有其局限,所以,劉可很快就進入了第二階段,把風格限定在不同色塊的均衡拌合之中,他的工作方式是用油漆反復堆疊出一條又一條的寬形長條色塊,堆疊的結果是色塊本身產生厚度,不同的厚度組成為一個整體,其中閃爍著的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淺度空間感。在這裡,劉可再次看到了肢解的機會,不過這一次他不是肢解物象,而是肢解平面,以及構成繪畫基本因素的齊整的邊框。從某種意義看,劉可的抽象是一種肢解的結果,甚至,他的藝術就是肢解本身。和劉可的肢解不同,任松一直嘗試在平面上積極地建構一些什麼出來,他是反復的,又是固執的。反復在於,他不知道如何才能確定繪畫語言本身的意義,這促使他不斷去放大個人對於色層堆疊的認知。固執在於,他始終對具象有一種難依難舍的依戀,讓自己徘徊在表現與抽象之間,直到有一天他終於發現了色層獨立的意義所在,那種長期糾纏於內心對於物象的迷思才得到了有效的清除,表現性才得以從物象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從而讓純化語言本身重新變成一種積極的實踐。
其實,把曾曦歸入抽象一類是有點勉強的。我的意思是說,抽象並不是他的創作衝動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否抽象從來都不構成他的一個問題。對於曾曦來說,觀看才是核心,而觀看的基礎不是美學,而是視網膜。正是視網膜本身構成了觀看的核心,從而為新的藝術確立與過往完全不同的方向,但事實上人們常常圍繞著一個關於藝術的假像爭論不休,面對一大堆脫離了觀看的虛構性審美焦慮萬分。曾曦強烈地希望回到本初,回到視覺藝術的原點,這一點頗有點現象學的意味在。也就是說,曾曦希望把意義懸置起來,讓價值脫離現場,做空眼前的一切,把視覺,進而把藝術還原為現象,然後才去思考。從某種意義看,我以為曾曦的思考本身就是作品,包含了抽象的全部可能性。
準確地說,抽象是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是有變化的。先前,抽象是對具象的反抗,是對工具性的顛覆,以期獲得一種形式主義意義上的思想解放。所有這一切均發生在老一輩藝術家的個體實踐當中,構成了他們從事抽象藝術的深層動機。然後,抽象作為物件漸次退隱,形式不再構成討論的重心,視覺在現象學的框架裡得到了重新定義的機會,藝術家也分別在藝術的各個層面上尋找新的領地。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擴張的氛圍中,藝術轉變為一個真正開放的體系,其中,抽象成為導引,成為懸置的契機,藝術家得以重新定義自我與社會、與歷史,乃至與藝術的關係,結果,抽象問題趁勢轉變為懸置有否有效的問題。就現象而言,真實的問題是,懸置本身能否導致真實的思想的產生。
要知道,沒有思想的產生,藝術就沒有意義。這才是根本的問題。
2017年12月4日初稿
2018年1月28日二稿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不代表香港01立場。
原題為 抽象作為一個問題:從《回歸本體:廣東三十年抽象型藝術回溯》展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