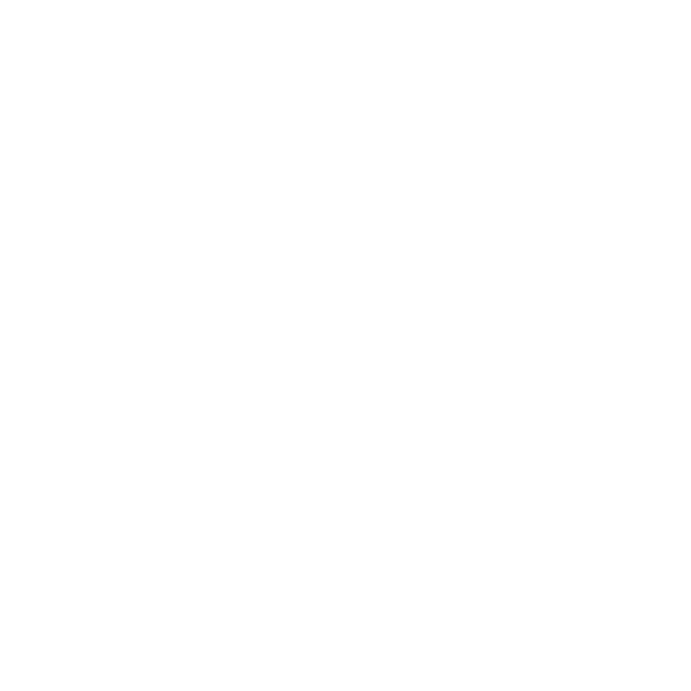【人生劇場】身體是自己唯一的藝術品 改變命運不靠別人
/ 2019.04.26
【文章原刊於01撐場,歡迎下載香港01 app,與更多作者一同討論喜愛話題。】
故事主角大專讀新聞系,畢業後卻跑到電視台當編劇,曾參與1980年代神劇《新紮師兄》系列的劇本創作。因緣際遇,他踏足劇場,談藝術論文化,探索生命、了解自己。聽來抽象,實情在今天,誰不需要?
吳偉碩舉手投足的舞者氣質,是入了血,屬於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資料圖片)
他是資深劇場演員、導演兼表演訓練老師,亦是於4月15日舉行、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主辦的2018年「劇評人獎」的年度導演獎得主 —— 吳偉碩(梵谷)。
「現在有人望着我,就覺得我是大師,感覺到那能量。」(《未來簡史》劇照)
吳偉碩高中畢業後,到樹仁學院(註1)選修新聞,是因為覺得新聞跟生活有關,也因為自小喜歡閱讀:「小學已常到圖書館、小童群益會裏鑽,愛看 《小王子》、《西遊記》之類,特別喜歡看故事。」他覺得,新聞報道被定義為報道文學,成為其中一種文學類型,特別有意思。「畢業那年,學系出版系刊,我當時是學生會會長,就寫了一篇文章紀念畢業的感覺,居然給評為有文學味道。」有因,才有果。
吳偉碩高中畢業後,到樹仁學院(註1)選修新聞,是因為覺得新聞跟生活有關,也因為自小喜歡閱讀。(網絡圖片)
為了賺取學費,吳偉碩在樹仁第二年,已經到《工商日報》(註2)當全職體育記者,主要寫足球,每天寫一兩篇稿,他視作為訓練。畢業實習,他到香港電台面試,歷屆同學一般申請到新聞或者公共事務等部門,他卻說要去電視戲劇組,「戲劇是說故事,創作的可能性比較大。」當年,他曾參與兒童劇《晴天雨天孩子天》等的劇本創作。
當年,他曾參與兒童劇《晴天雨天孩子天》等的劇本創作。(《晴天雨天孩子天》劇照)
他說當初有想過要當導演,「實習的過程中,漸漸發覺劇本才是決定內容的手段,就像用什麼文學形式去說故事般。」畢業後,他加入了無綫電視當編劇,前後6年,參與劇本創作包括《新紮師兄》系列等。
畢業後,他加入了無綫電視當編劇,前後6年,參與劇本創作包括《新紮師兄》系列等。(《新紮師兄》劇照)
浸在那大眾趣味的氛圍下,吳偉碩漸漸感到厭倦,亦不難想像。「當年,放工就去學習現代舞和水彩畫,純粹有興趣,兩種都喜歡。」只是,後來他選了專注現代舞,也引領他步往另一階段。
「第一次感到杯有重量」
吳偉碩當初學跳現代舞,還有個逗趣的故事。「畢業那年,(樹仁新聞)系會舉辦聖誕派對,同學選跳一段 《白毛女》,有位女同學拿着地拖模仿白毛女,另一個男同學要來個big jump,怎料跣腳,一滑就滑到台側,大家覺得好笑又有趣,也是第一次跟男同學跳舞。」然後,大家興致勃勃的,一齊去學跳現代舞。最後,就只剩下他,有堅持下去。
習舞後,驚艷是:「第一次拿起水杯,感覺到那重量。」他形容,以往的自己是哲學思維,講究邏輯,「原來忽略了身體、生命的感覺。」與現代舞初相逢,讓他得到嶄新的感悟:「感受、感覺,不是靠思考,而是透過生活基本的接觸。」
那時,他習舞之餘,亦盼望對現代舞有更深入的認識。「當年的報紙、藝術媒介,都甚少談及現代舞。」他卻在樹仁位於灣仔的舊校舍,發現有家美國圖書館,擁有藏量豐富的舞蹈錄影帶,「我就像發現金礦般,總是留在那處,不停地看。」也由那時開始,他以梵谷為筆名,先後在星島日報及信報文化版,撰寫有關舞蹈的評論。
「感受、感覺,不是靠思考,而是透過生活基本的接觸。」(鄧樹榮工作室戲劇《馬克白》劇照)
點與點 連成線
在一次訪問中,他認識了演藝學院兩位第一屆畢業生,張達明和陳炳釗,並獲邀加入他們組成的實驗劇團「沙磚上」(註3),這個劇團獲城市當代舞蹈團支持。
吳偉碩形容,當年劇團理念前衞,不設藝術總監,「不想由人支配劇團,大家輪流當導演,一起討論,表演形式較着重意識形態,而非故事發展。」他打趣說,所謂的後現代理論:「是看完了,也不知在談什麼。」然而,他亦因此走到人生的拐點。
當時,他還在無綫當編劇,也有在學現代舞,又參與劇團的演出,「卻有點覺得格格不入,我這個是跳舞的身體,雖然明白動作的意義,但就不知道怎樣跟戲劇拉在一起。」由於無法找到答案,他加入劇團兩年後,就沒有再參與演出,後來還辭掉無綫編劇的工作。
有兩年,他沒有正職,就是想讓心靜下來。直到有線電視籌備開台,他在朋友引薦下,加入其中一個國際藝術文化頻道。「因為要預備買片,所以每天在節目catalogue(目錄)中揀片看。」他就特別挑跳舞的,其中一齣法國的節目,是談100年以來,舞蹈在歐洲和美國的文化發展和演變,由古典芭蕾舞談到現代舞,以至後現代舞,還有從創作者的角度回應社會變化,讓他大開眼界。
有兩年,他沒有正職,就是想讓心靜下來。(何.必館《最後一次西遊 — 走在曼陀羅邊緣上》劇照)
不是思考,要經歷和感覺
吳偉碩說,當時他明白到,表演藝術所呈現的身體,並不單純是身體本身,還載着生活習慣、背後的思想。隨後,他開展劇場的演出,伯樂是在美國侯斯頓大學修讀戲劇的何應豐。那年是1995年,二人在訪問後認識,一見如故。
「他知道我是跳舞的,又寫戲劇,覺得可以一試;當時我們每星期都有兩三晚到CCDC(城市當代舞蹈團)studio 試演,沒有劇本,他說做什麼,我便做什麼,他主要看我如何在身體找到真實的感覺。」
他說接受傳統戲劇訓練的演員,沒有創作的概念,「身體背後是有內容、質感的,有了感覺、經歷,會出現創作,不是站着就可以寫出劇本。」
表演藝術所呈現的身體,並不單純是身體本身,還載着生活習慣、背後的思想。(圖片自馬戲班)
自1995年,他便加入何應豐的劇團「瘋祭舞台」,並在多個演出中擔任要角,也是他口中「透過身體explore(發掘)自己的可能性」。他也談起自己信任身體的經歷,那是他辭去正職的兩年。「當時也因為感情的問題,有了depression(抑鬱症),但覺得不可以讓精神處於那沉溺的狀態,所以逼自己去跑步,讓自己重拾活力,克服情緒。」他的體驗是,只要信任身體,便可以改造自己:「身體賦予力量,讓自己think positively(正面思考),有自信和力量,去support(支持)自己。」
1997年,他在中環波老道中英劇團排過戲後,就到英國倫敦密德薩斯大學,修讀東西方戲劇比較碩士課程。及至2000年,他再到新加坡實踐表演藝術學院,修讀由郭寶崑創辦「劇場訓練與研究課程」,先後學習日本能劇、中國京劇、印度Bharatanatyam神殿舞及印尼畦宮廷舞蹈Wayang Wong各半年,以及當代表演體系的訓練。
吳偉碩說,課程讓他感悟到深入傳統,才找到生命:「想起25歲才學跳舞,穿起舞衣,在鏡中看自己,覺得像極『耕田佬』;後來逼自己練習,現在手揚起,那動作的感覺都已在。」他就是讓身體有所經歷,然後才明白這門藝術,以至生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就如上山修行般,現在有人望着我,就覺得我是大師,感覺到那能量;以為我浸了很多年,那實在是身體的經歷,透過傳統的訓練,讓自己沒有做戲,但已經有這個being(存在)。」那就是一舉手一投足,人在戲在。
他就是讓身體有所經歷,然後才明白這門藝術,以至生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馬戲班《墨迷宮》劇照)
種在自己身上的,也希望種在香港人身上
回港後,吳偉碩也沒想過生計,就全身投入舞台表演,「最初沒有錢,nude model(裸體模特兒)也做過,也試過要問朋友借錢開飯。」他說遇到老師郭寶崑前,曾經感到很迷惘,但課程帶給他的感悟,就是「真正影響自己,其實是自己,要認真對待生命,要有動力去追尋,因為你是自己唯一的藝術品。」他心想:「我想追尋人生,應該都有其他人想吧?一個需要就一個,十個就十個。」
2007年,他成立香港表演研究中心,擔任藝術總監及主研究員,並完成了《太極與表演訓練關係》的第一部分研究工作;又憑過去訓練、研究和教學的經驗,整理出一套結合心理和身體運用的「心體一技」訓練系統。
在訓練過程,吳偉碩強調不會去主動解釋,「生命在自己手上,怎可以總是靠他人幫助?」他認為,藝術要抱開放態度:「認真地由自己出發,自己尋找答案,因為獲得最大benefits(好處)是自己。」
一路走來,吳偉碩沒有說過自己苦,那兩年的抑鬱亦只輕輕帶過。誰不知道,藝術路難行,但用他的話,只要認真對待,易行又好,難行也好,就一直追尋到底。那不更美好嗎?
只要是信任身體,便可以改造自己。
誰不知道,藝術路難行,但用他的話,只要認真對待,易行又好,難行也好,就一直追尋到底。那不更美好嗎?(作者提供)
場地鳴謝:room68
攝影:Trevor Tse
編輯:堂
註1:樹仁學院於2006年升格為樹仁大學
註2:台資工商日報於1925年7月創刊,由何世禮主理,於1984年11月停刊。
註3:盧偉力 (2012) 《當代香港戲劇的文化政治與美學實踐——兼談幾個本土後現代主義範式》
作者簡介:陳零
現為新媒體《一點》作者。《一點》以中英文記錄香港人的故事,有你多一點。
作者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hanling0/
【編按:文章題目為編輯所擬,原題為「吳偉碩 : 你是自己唯一的藝術品」】
(以上文章內容均屬用戶提供,香港01不為任何用戶內容而衍生或遭受之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