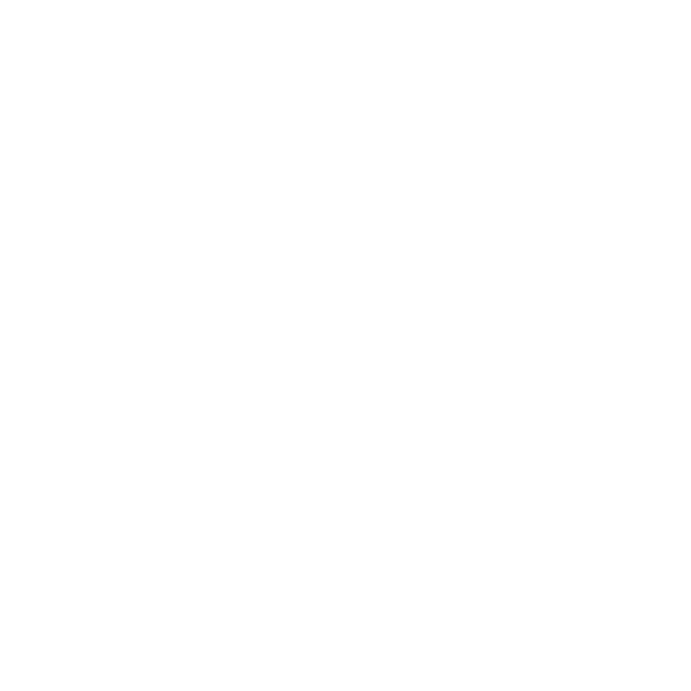狂舞派的十年 黃修平:拍電影性價比極低 文化人創作者付出極大
/ 2021.03.01
黃修平導演(攝影:黃寶瑩)
在十年前《狂舞派》還未出現,最初的舞者會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邊的一塊空地練習、Battle,後來這「聖地」卻被不斷淋濕、管理員屢次阻止他們跳舞,最後一眾舞者由街頭走入工廠,已是一個悲哀。再看今集,連工廠這個容身之地也被逼走。無獨有偶,《狂舞派》的靈感起源——PolyU便利店外的空地,也是一個街舞聖地,遭受同樣命運。
「打壓自由的原因總是存在,是否真的無可避免?」(攝影:黃寶瑩)
這個故事就由導演再重溫:「大約在2008年,當時有機會可以拍下一套戲,由於我們沒有辦公室,經常與監製陳心遙到處坐街談公事。那時我一直在PolyU兼職教書,於是有一次就在學校約見,遇到有不少人在便利店外這塊『聖地』跳舞,不只是學校Dance Society的成員,也有來自五湖四海甚至外國舞者都會到來。後來知道的故事就是:因為Dance Society被打壓所以沒有『So房』,他們就發揮街舞精神在此練習,也是生命力的表現。不過當年就曾被禁過,我親眼見到一個我認為很針對性的警示牌:一個打上交叉的B-Boy剪影。直到後來《狂1》出現,我們到處謝票時也會講及這個故事,因為正是電影的靈感來源,可能這對於校方而言也是一個好的形象,還記得在1,000萬票房那天,PolyU學生會就爭取到重開這聖地可以跳舞,可惜好景不常,直到2018年準備開拍新作時,我在選角時就從來自PolyU的舞者得知那裡又被禁了,後來連聯校跳舞比賽亦不復存在,我只覺得打壓自由的原因總是存在,是否真的無可避免?大學有不少與公眾共生的例子,以前有人教太極班,《狂1》的太極元素也是從此而來的,有不少人在內攝影、甚至Cosplay等,可惜相信已經難以重拾這光景了。我只希望如果有機會有一些方法可以『吊著鹽水』地做下去。」
「其實人非草木,爭執是一定存在,要思考的是爭執會否大到無朋友做」(攝影:黃寶瑩)
在《狂1》Baby John飾演的阿良原是備受討好的角色,可惜來到今集卻成為反派,戲中一幕,他為財團老闆擋雞蛋,及後被渲染為立功,但他的角色本設計得別具人性,擋雞蛋的行為其實是否只是他的人性所在?正如他會幫助執紙皮婆婆,由心出發做事是否也要考慮?「由於社會的上層出現問題,下層的壓力太大,自然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衝突,甚至割席,愈演愈烈。社會給予的空間太少,下層又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空間,變成自己批鬥自己。其實人非草木,爭執是一定存在,要思考的是爭執會否大到無朋友做,可不可以做到和而不同呢。」
(攝影:黃寶瑩)
戲中阿良也有想過,藉著放大自己的力量去幫助到更多的人,結果還是不符期望,到底他是否懷有一顆赤子之心?這種想法又是否現實?「從表面來看阿良這個角色都是反派,但現實上很多我們指罵為混蛋的人真的是大奸大惡嗎?現實上好多人想左右逢源,想從狹縫中爭取到一些利益但到頭來都失敗,很多這些的例子,也有很多人以為自己是這樣的,在我看來並不赤子。或者最核心的想法是赤子,卻混雜了很多雜質,我對此並無批判的。」
(攝影:黃寶瑩)
上回都說過,在香港拍電影殊不容易,《狂舞派》之所以動人,也因為某程度上夠真實,例如戲中見證到一眾藝術創作者如何在生活中苦苦追求創作的養分,對於導演而言創作最奢侈的是還是自由與時間:「聽過不少電影人說笑道,如果我們用花在拍電影的精力去炒股票,很可能發大達吧!拍電影是性價比極低的工作,真的要算起來可能連最低工資都達不到。如果想在人生入面成就一些事,我們無時無刻的思考都會與作品有關,這是最奢侈的。我並非完全與賺錢的話題和事絕緣,我也相信很多人在社會上都被輕視了,其實他們都有相對心血的付出,正因如此這才是這部戲感動到人之處,不只是戲中的工廈人,我亦收到很多人跟我說在戲中看到自己。」
狂舞派3劇照
最後,無疑香港有著重重壓力,問及導演如何從中放鬆,他指出一件渴望已久的事,終於在疫情期間實現了:「說到放鬆,我對而言一定是禪修、行山。但在疫症期間亦有一件事是令我別具感受亦非常解壓的,就是砌模型。我小時候曾經十分醉心於此,曾幾何時日日追著,但長大放低了之後卻沒有任何一件東西留下,這是最遺撼的。所以早前我決心放下電影,一砌之下一發不可收拾,期間的過程是很平靜的,因為判斷非常清晰,又知道總有做得到的時候,有很多創意、方法去達成更符合自己想成就的模樣。最重要的是,這件作品只需要滿足自己,自己覺得開心就足夠。」